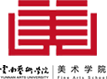关于武俊艺术的座谈
参加者:毛旭辉 武 俊 张光华
时间:2007年10月4日—2007年10月6日
地点:昆明 武俊工作室
文字整理:张光华
这是一个有果盘、果汁和普洱茶享用的三个人的小型座谈,在四周摆满了飘浮着年轻女人体作品的武俊的画室内,毛旭辉先生和武俊先生一边潜心交谈,一边悠然吐纳着烟圈。对于张光华这个小丫头来说,也有自己陶醉的方式,那就是认真聆听两位前辈谈他们对艺术和人生的感悟,听他们偶尔穿插进来的那些尘封至醇的精彩往事。伴随着两位先生的讲述,小丫头也在渐渐增强的悬浮感中飘了起来,在一只白天鹅的引领下,穿梭于古代文物的出土场和E时代的数据之城中间,她不时地欣赏着摩天大楼冷峻的玻璃窗中反映出的自己飘在空中的美丽形态,她坚信这个美丽的影像是她的,但是那双鹰隼一样孤傲的眼睛,又让她浑身颤抖,她不禁怀疑这是她吗?于是她转向旁边的楼宇,找到了像自己一样正在漂浮的同伴,她们的美丽面庞上同样是那冰一样的神情,她不仅陷入了一种寂静的沉思当中。
一、 “出走”
张:武老师,您和毛老师是在云南艺术学院学习时候的同班同学,同窗同宿舍四年,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没有和他一起从事85现代艺术思潮,而是在九十年代才开始当代艺术创作并直到今天?
武: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然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张:您能仔细讲来听听吗?
武:当年上大学时,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平时都是被班上的这些大哥们抹着头玩儿。成绩也只是处于中等,不像毛老师他们,名列前茅。按道理来说,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哪里去,留校的机会是怎么都不会轮到我头上的。说来真是造化弄人,大四那年,在时隔多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云艺又新招进一个班来,学校领导非常高兴,决定开茶话会欢迎他们。于是校领导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买茶话会所需要的食品,不幸的是,回来的路上就被一辆汽车给迎面撞飞了。
毛:就是现在西站旁边的铁路边上。
武:对,就是那里。我的左腿被撞成粉碎性骨折,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这次受伤也就当然的被学校定性为工伤。与此同时,毛老师和其它同学正在紧张的进行毕业创作。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医院治疗,后来转到了省地质局疗养院。我的毕业创作也就是这段时间在疗养院里完成的,画了一张小画,但后来得到的评价还不错。
毛:是的,他的毕业创作在我们班上是比较好的。
武:当时毛老师正在构思画一组大型组画,我被困在医院里就没有想那么多。在医院那种极重视清洁的地方,画画是一件很脏的事情,但是那些小护士却没有跟我过不去。一个瘸腿小伙子在医院里带伤创作,这也算是一件稀罕事。在我们班的毕业展览之后,《云南日报》选择了一些作品刊登了出来,其中就有我的作品。在当时,能上省报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是件大事!这些小护士看了更是惊讶,她们于是明白了,原来艺术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毕业后,大家都分配了,就我一个人被压了下来。因为学校当时决定把我分配到省地质局,这是把我撞伤的那部车子所属的单位,(也是潘德海老师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单位)。但是他们以我瘸着腿还要站讲台不太合适为由,一直拒绝接受我。
毛:要不然,你就和潘德海是同事了,哈哈……
武:在焦急的等待了半年之后,学校答应安排我留校。但是又没有留校名额,报上级单位也不批,后来的变化就更戏剧性了。当时川美一位朋友叫马祥生,本来是要毕业留校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留校的事情被耽搁了。后来准备把老马安排进云艺,但是云艺反过来以已经没有了分配名额为由不接收,教育厅只好答应只要云艺接收老马,他们就在拨一个名额给云艺,也就是给我,于是我们俩就同时进了云艺。
毛:这也就是老天的安排啊,让你在原地转了个小圈圈。
武:对呀,真是戏剧性的。
张:这其中命运的安排,是不是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您后来没有进入到八十年代的青年美术思潮的原因呢?
武:是的,对于我来说,能够留在学院已经是一件很侥幸的事情。如果你达不到学院教学的技术水准和其它素质要求,没有能力,怎么能呆下去?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下定决心要在学院这条路上奔,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事就是努力去提高自己。八十年代的青年美术运动期间,现代主义得到迅猛的发展,我也经常参加一些大毛和张晓刚他们组织的集体活动,常常一起喝酒谈艺术,受他们的感染很多,但是我个人的准备总是不够,总感觉自己切不进去。实际上, 1986年在“西南艺术群体”的影响下,云南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也组织了一个名称为“南蛮子”的艺术群体,我也做了一些抽象表现主义的摸索。但是在大家举办了展览之后,很快就被学校打压了。因此,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毛:八十年代中国的学院是非常保守的。
武:到了90年代,进入到后现代这样一个混杂的文化时代,传统也好,学院也好,都能够自然的成为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学院中,包括中央美术学院、四川以及云南艺术学院等,也尝试把当代艺术文化引入到学院教学中。1996年,大毛、唐志冈和我一起共同组建了油画第二工作室,培养了不少年轻艺术家,为推动云南的当代艺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张:那从82年云艺毕业到93年去北京进修之前的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呢?
武:大学毕业的十年间,我一直在做基础语言的研究,创作一些云南乡土人物和历史题材等主题性绘画,偏重表现的绘画风格。而且我那段时期的做品很少个人的意识,喜欢画一堆人,表现一种群体性。代表作品有《土布》和《山顶上的人们》组画等。所以,大毛对我从央美回来后的改变,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总结,说我是从云南“风情”中出走。
张:您能具体谈谈您自己对 “出走”的理解吗?
武:为什么会在90年代?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悟,是我个人被文化的一些触动。90年代的显著特点就是,艺术的方式、文化的方式、生活的方式都已经比较多元化,体现出后现代的征兆。而传统也从以前被批判、反叛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新的可用对象,成为一种可挪用的文化形态。我以前的一些生活经验、文化经验和时代经验,告诉我必须从这个转折期找到进入这个时代的切口。而在北京的学习经历,恰好让我找到了这个切口。
张:那您又是在何种机缘下,出于何种选择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学习的呢?
武:其实我1987年的时候就去考过一次这个进修班,但是没有成功。当时这个研修班是很难考的。后来我是在唐志冈的帮助下才去的央美。当时老唐刚好从北京回来,放眼一看说“云南没有画油画的”。于是我就请他到班上去代课,大家一起画。他有一个校友高天雄在中央美院油画系读研,老唐介绍我去找他,高老师看过我的素描指出了很多问题。通过努力,我终于如愿进了中央美院。
张:您当时去进修,就是很明确的要把这次机会当作一个切口和机会,更接近当代艺术,转换一下创作方向呢?还是想在学院的层面上更进一步?
武:当时纯粹就是出于学院层面上的考虑,因为当时中央美院是中国学院派的实力代表,想去了以后再把“学院”认识透彻一些。结果只用了半年就清楚了。然后接触到的是大量的国际当代艺术信息和艺术作品。后边的一年就不再安安静静的在教室画课堂作业了,开始到处跑,到处看各种各样的展览,再加上班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小的同学,思维比较活跃,我经常和他们讨论艺术问题,于是就促生了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共同趋向。我的毕业创作《九色·碎片》,就是在新表现主义风格的基础上,把图片、木材等都拼贴到作品之中。想在这种拼贴的组合实验中慢慢走向语言的纯粹,更加努力去贴近当代文化的感觉。
张:从那幅作品开始,正在被人们遗忘的文化符号——出土文物、凤冠霞帔、带着荣誉红花的中山装,和残肢断体、牡丹琼芳、钢铁工具、扭曲抽动的布块,以及像外星人一样从画外空间中探进来的女人脑袋,颠倒错乱的出现在你的作品中,这种新表现主义的风格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2000年开始,您作品中的符号在减少的同时明确了许多,画面表现出的焦虑感也更加强烈,然而与此同时您画得也越来越少,尤其是2003年的作品画面中的物象减少到只有一个女人体,直到2005年转入到新的表现风格开始,这种现象才发生了改变。您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那段时间您在做什么呢?
武:我在创作每一组作品时都会长时间的被事先设想好的或者正在表现的画中意象萦绕,就像生活在其中一样,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体验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时间的先后是可以被忽略掉的,然而作品自身的变化反而又会把这些体验过程按时间顺序呈现出来。我对作品中所选用的这些物象,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体验,亲眼看到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中被创造或毁灭的过程。其实我的作品一直是很苦涩的,但是在2000年左右,我发现在不知不觉中,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周围彻底消失了,我顿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感到无比的痛苦,渴望找到解决这种痛苦的方式。有一天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时,一幅画上的云南青铜器让我的视线凝滞了。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命意识是如此之强烈,哪怕只是一颗纽扣,都要做成人与兽、畜与兽激烈撕咬的纹样,这不只是装饰的需要,而是对生命的热忱赞美。于是我停下来试图重新回归到“生命流”的起点,经常找毛老师他们聊天探讨学术。当然,我在这几年中,做了一些理论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关于云南当代艺术史、民族文化语境以及教育等诸问题的研究。出版了《美术问题》、《民间天空—云南当代美术档案》、《云南高等美术教育史》等著作。经过这段时间的沉静与思考之后,我没有继续选择表现主义,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真正的当代。
毛:从这种思想根源上来说,这算是你的第二次“出走”,哈哈……
二、“无意识”
毛:现在看来,你早期的人物写生作品,从构成上来说,与你现在的的作品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你们来看,这几幅人体写生作品中人物的脚都是悬浮的。但是按照写实的处理要求,这几只脚都应该是坚实的扎在画面上的。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错误,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是画家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这种无意识就给你后面的作品,那些飘浮的“城市候鸟”,提供了一种轨迹证明。
武:对,现在看来,9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也都延续着这种特点,我当时创作这些作品时倒真是没有意识到。
毛:实际上,某种无意识的东西也是具有创造性的,都是与我们的艺术有关系的。然后,这种无意识的东西从原来的模糊形态中突显,越来越放大,就成为每位个体艺术家很重要的创作特征,成为能够代表这个艺术家个体特质的符号。悬浮感,现在你整个画面中都是这种悬浮感,这也就是你作品的特质了。
武:你说的很有道理,可能就是我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引发了后面的悬浮感,《九色·碎片》这件作品是一个起点,人物一飘上去,这种悬浮感就一下子变得突出和强烈了。在后来的作品中,画面中的人物就都是飘浮的了。
毛:这就刚好证明了时间对作品的证明问题。有些作品是需要通过时间和过程去证明的,需要在与后面作品的对比中被突显出来。因为通常情况下,后面的作品都是在证明前面作品中已经存在的一些还未命名的因素和特质,当然,前面的一些作品也会反过来证明后面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种相互关联、相互辩证的价值体现过程。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做回顾展很有意义,因为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整条创作线索,可能是一条精神线索,也可能是一条语言线索,而这才是永远值得去讨论和分析的东西,脱离了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停留在对表皮的认识。我也只能暂时把你早期画面中体现出的这种无意识,理解为与你的价值观有关系。为什么本该扎实的地方反而悬了起来?为什么两只脚会一只是踩实的而另一只却是飘的?很显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问题。
武:无意识的选择也说明了一种经验的渐渐积累。
毛:在你的画面中还有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就是画面物体的扭曲感。从早期绘画中的一个小小的笔触到一块衬布,再到现在画面中的空间分隔线,都是倾斜扭曲的,找不到一条并行线或垂直线。但是这种扭曲的线条却正好与那些美女的姿态配合的很和谐,也或者说,这些女孩儿的姿态就是从你这种扭曲的潜意识中一点点的生发出来的。我们应该对这种“扭动”和“飘浮”进行探讨,它们为什么会从你的潜意识中产生出来?它们作为一种绘画语言与审美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们是否隐含了生存的终极问题?或许这就你在特殊的生活背景中产生的特殊感受,是你对今天生活环境的独特体验和价值关照。因为同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每个人对时代的体验却各不相同,各自不同的生活体验才使不同的艺术家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绘画语言。就像岳敏君那甜蜜的傻乎乎的“笑脸”,因为他说过人只有在笑的时候,大脑才会暂时的停止思考,所以,“笑”就成为了他的绘画语言。而张晓刚的“严肃”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关照,而具有某种历史感。
张:武老师,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您画中的衣服,虽然只是作为独立的没有依附于人的身体上的衣服,但是我却从它那极为有张力的形态变化中感觉到一种生命动势,这种动势从您早期的画中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就像是穿在一位隐形的美女的身体上一样。我想请教您为什么会这样处理,您是不是想要暗示或隐藏什么?
武:这可能也是我内心无意识的一种外在显现吧。我是在对衣服的图像表现中,也就是在衣服与女人体的物质实体进行的视觉对比中,在这种“扭曲”的潜行形态的释放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把衣服画的飘了起来,就在我忽然间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同时发现飘动的衣服与女人体不仅有着紧密联系,也存在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内心欲望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距离。衣服在满足了我们的某种需要的同时,我们也赋予了衣服更多的含义,它也在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阐释人性。我的这个认识后来就转化为一种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我对衣服的生命运动性的刻画就越来越饱满,除了没有手没有头之外,它们不再是悬挂的空的衣服,而是有生命存在的富有动感的衣服。
3、 游离
毛:阿华,你觉得武老师的画色情吗?
张:我认为还是有一些色情,尤其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画时,这种看法最强烈。但是后面想想,一个女孩儿在自己的私密空间内展示一下自己的姿色,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那种色情的感觉就渐渐变淡了。
毛:但是这些作品是为公众空间创作的,是要面对公众的呀,那就跟在个人私密空间中的关照方式不一样了。
张:我还想听听武老师自己的看法。您赞成毛老师的这个观点吗?
武:公众空间必不可少是要面对的,我目前的这一类以女性裸体为主要符号的作品,在受众
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但这不会影响我的创作以及一些公众性比较强的空间的接纳。李季、老唐和毛老师的作品就有广阔的受众空间,他们的画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毛:这倒也不是,其实任何一种绘画语言都需要找到适合它的受众空间,我的“剪刀”也不是受所有人的欢迎。曾经就有朋友回馈信息给我,说在一些比较重视风水文化的城市和家庭,有些人认为挂一把“剪刀”在家里,会破坏掉家里的风水。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剪刀”太锋利了吧?哈哈……但是,我们总不能去为了照应所有人的看法而牺牲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们的绘画语言只有在坚持中才能更鲜明。
武:毛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关于是否色情的问题,大毛以前就问过我一次。当时我已经在创作《城市候鸟》,毛老师看过我的画后问我,有没有在画的时候想到色情?我说,肯定有的,因为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对欲望的一种表达。这些像候鸟一样的城市人类,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狭小空间内,裸露,宣泄欲望和情绪,这是一种存在的方式。
毛:在你的作品中,有些人物的手势安排总是会伸出一只食指,有什么特殊的含意吗?
武: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安排。或许,也有一定的所指吧,在她们的身体的周遭(画面看不到的地方)存在着一些什么东西。就象这些动势强烈的飘浮的躯体,所体现出来的很含蓄很隐晦的表达方式。
毛:我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西南艺术家所持有的一种特质,大家都在研究语言形式与情感表达的关系。叶永青的创作也好,张晓刚的创作也好,潘德海的创作也好,都选择了通过一种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深层的含义。这种特质在与政治波普等其它艺术群体和其它地方的艺术家语言风格的对比中,就更加明显了。即使像刘建华的作品,虽然采用了艳丽的色彩等强烈的视觉传达方式,但它要表达的思想却并没有在这种形式中凸显和直白化,而是需要观众在感官的冲动慢慢冷静下来之后,去一点一点的感觉和发现。
张:听过了我们的看法之后,除了刚才已经谈到的含蓄的情色话题,毛老师对武老师的作品还有其它的感觉和看法吗?
毛:其实在刚才我们谈到的有关作品是否被接受的问题中,我的最终认识是,我们的作品已经被公众当成了一种风景。我的剪刀是风景,武俊的美女也是风景。只不过这些美女是平时游走在城市中的,作为各种社会角色的风景,是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风景。推销需要美女,公关需要美女,艺术空间的讲解员需要美女……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需要,我们无法说清楚这种现象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我能肯定它一定隐含着某种含义。举你的画为例,当我在欣赏画中这些美丽的“风光”时,总会有一种容颜衰退、青春消逝的黯伤浮上我的心头,眼前的美丽也就更加能引起我的怜惜。青春总是短暂的。
张:虽然作为一个女孩儿,我有些嫉妒她们的美丽,但是我也真实地体会到了这种逝去的感伤。然而,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从她们的表情中,我根本读不到任何信息,不知道除了示美以外她们那酷的有些呆滞的脸上到底写着什么?
毛:不仅是你读不出,我也感到有些困惑。这些女孩儿脸上带着一副90年代后期以后出现的流行表情,从感官上来看她们很漂亮,性感的身材、光滑的皮肤、娇好的脸庞,但是眼神里却传出一股强烈的冷漠,给人一种遥远的距离感,让我们无法接近她们,无法与她们沟通,我想最能用来形容这种感觉的词就是“游离”了。游离即不确定,不确定她们在表达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与她们沟通,只知道她们是这个地球上的人,但是却飘在我们的思想可与之交流的平台之外。这可能就是当代,就是美女时代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然而这种引力反作用于我们的距离感也是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坐在这里,忽然面前出现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年轻女模特,我们不知该如何和她交流一样。
张:对,在这个封闭的几何形空间中,她们的这种冰冷的表情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压抑和寂静。还有这一件件皮质或类似塑料一样的衣服,在强烈扭动中,产生许多比较结实的褶皱,在光的作用下显得是那么锋利,锐化了这个封闭空间中生命运动与时间凝滞的矛盾,与女孩儿冷酷的知性气质和压抑的空间共同营造出一个游离的时空。
作者间介:
毛旭辉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中国著名艺术家
武 俊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油画系主任
张光华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艺]蕴心集—云南大学出版社